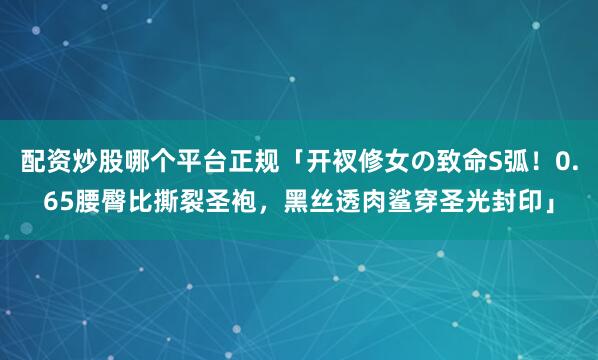首长令我见邱会作
作者:王波
1998年的初春,春意盎然,阳光明媚,柳树抽出了嫩绿的嫩芽,枝条也仿佛披上了翠绿的盛装。院落中弥漫着一片宁静。
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首长亲自将我唤至他的办公室。他惯常地用大手轻轻擦拭了一下面颊,沉思片刻,接着说道:
“你曾提到我们的回忆录资料尚不充足,其中涉及新四军3师的历史以及解放后总后的内容。关于新四军3师的部分,你已联系过吴法宪。至于解放后的那段,建议你前往西安寻找邱会作。”
我惊讶地询问道:“首长,您是打算前往西安寻找邱会作吗?”
领导表示:“关于‘黄吴李邱’的待遇问题,我们已妥善处理。他现在享受副省级待遇,并居住在省委大院。请你去找他,他或许能向我们透露一些相关情况。”
首长所提及的待遇问题,实则关乎于1987年秋季,我同抗战时期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三位作战参谋之间的周旋。这三位分别是“成空”周旋副参谋长以及“南空”薛毓芳副参谋长。(红军)和通讯兵李部长”(皆为副军职)我前往济南一处工人宿舍区拜访吴法宪。他居于一套面积略大于五十平方米的居所,其空间大小相当于军队中营级干部的住所。吴法宪表达了他的困境,他面临着医疗上的极大难题,恳请洪能协助他解决医疗方面的难题。
我返程后即刻向首长进行了汇报,并遵照首长的指示,现场迅速书写了一张白纸条。(无公函字头)首长将此批示交由杨副主席审批。杨副主席转请中央审议,中央作出决策:“黄、吴、李、邱”四位同志将享受副省级的待遇提升。

邱会作、吴法宪、黄永胜、李作鹏
肩负着“圣旨”的使命,我踏上飞往西安的旅程。在航班上,我的脑海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疑问——这次的任务能否圆满完成。回想起1971年1月,我初入机关时,常常在院子里遇见邱会作部长忙碌的身影。他总是习惯性地双手背于身后,挺拔的身姿,步履坚定而迅速。身后约一米处,是他的警卫员小朱紧随其后。偶尔,他会乘坐装饰着三面红旗的轿车,从西门驶来。我们都清楚,这样的车辆仅限于政治局委员乘坐。
真令人意外,当我踏入办公区西门时,门卫竟向我行礼,让我顿时感到尴尬。随后来到南小门,同样的情况再次上演。当我询问众人为何如此时,他们告诉我,我长得与副部长陈庞相似。更令人惊讶的是,还有人说我像张春桥。真是奇了怪了。
邱会作麾下有“三大干将”,分别是“陈王戴”,其中两位担任副部长,另一位则身兼副政委之职,皆以精明能干著称。在秦城解除囚禁后,我与另一位同志分别将他们送至南昌、沈阳与太原。
陈庞从秦城监狱获释后,径直前往北京站。与此同时,我们也安排了他的夫人及女儿一同前往。这对他们而言,是多年来的首次团聚。然而,从他们的言谈举止间,却难以察觉到他们刚刚重逢。他们畅谈古今,述说家常,讨论社会热点,气氛轻松愉悦,一家三口其乐融融,竟无人提及“913”事件或秦城往事。这让我心中暗自感到惊讶。他的女儿提到,天安门女出租车事件中的女司机正是她的同事,容貌颇为靓丽。她们并未避讳我,我则笑眯眯地聆听着他们的对话。
抵达南昌后,我与当地的驻军单位进行了交涉:请务必避免将他们安排在低楼层,南昌地区的潮湿气候对健康不利,二楼的环境相对更适宜。这一代人,在战争年代均有过卓越的功勋。在生活、医疗和居住等方面,我们必须细心关照他们。不久之后,我听说陈庞在南昌致力于永动机的研究,但遗憾的是,并未取得任何科研成果。我对南昌的小樟树苗情有独钟,当地的居民帮我挖掘了一株。然而,当我将这株小樟树带回京城种植于花盆中时,叶子却干枯了。看来,任何事物都需要适宜的条件。小樟树苗对生长环境的要求相当苛刻,它需要南方湿润的气候和富含红壤的土地。
抵达西安后,我投宿于203军部招待所。安顿下来不久,便迅速拨通了陕西省委老干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,是通过省委总机转接的。局长接通电话后,热情洋溢地答应立刻为我联系邱会作。
随即,局长便向我传达了情况不容乐观的消息。邱会作指出,“自那之后,我未曾再见后来者。此生,我誓不再踏入总后的门槛!”局长宣称,他乃是谁谁派来之人,今欲与你商讨一二事宜。邱会作回应道,不论谁派来都不见!
哇,真是出乎意料!这样的情形,我只好去秦始皇陵游览一番,顺便在地摊上挑选了几件古玩,最后都送给同学们了。边走边琢磨着如何想出对策。毕竟,我得回去向领导汇报情况啊。
抵达招待所后,我迅速拨通了老干局局长的电话。意想不到的是,局长已成功说服了邱会作。局长在电话中说道:“你不接见是不对的。他是受组织派遣来西安的,你应该予以接见。至于会见的具体内容,不论多少,那是你的自由。”邱会作回应道:“哦?既然如此,那就见一面吧。”于是,我与局长迅速商定,约定第二天上午九点,我将在省委大院指定的楼号接待邱会作。
“传闻长安如棋局,百年兴衰令人叹惋。”西安之地,实非贬谪官员养老之所。世事如同棋局,变化莫测,常易引发感伤之情,进而影响心境。
西安的气温相较北京高出3度以上,且湿度更为丰沛。常青藤已抽出嫩绿的枝芽,四周草色葱葱,繁花点缀其间,野草亦比北京更为繁茂。漫步于大小雁塔之间,感受着湿润而宜人的空气,这里无疑是历经“周秦汉晋隋唐”等十三朝古都的荣耀之地。
我准时敲响了邱会作房间的门,一位男士应声而出。他事先已知我前来拜访邱会作,随即示意我入座,并在一间宽敞的长方形客厅中稍作等待。

邱会作、胡敏及儿子一家
经过10分钟的等待,紧接着又是10分钟的沉默,我并未催促,对方也保持静坐。又过了5分钟,左侧的门缓缓打开,一位熟悉的人影映入眼帘。邱会作立刻问道:“是谁在找我?”
我猛地一站,笔直挺立,举手敬礼!朗声报告道:“邱老,我来拜访。”
他瞥了我一眼,嘴角带着一丝不自在,“邱老”,这称呼真是让人不舒服。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他径直前行,背着手,步伐坚定,直奔客厅西侧,又转身回来。他并未直视我,声音严肃地问道:“有何事相询?”在营造出紧张氛围后,他再次投来目光,“是你找我吗?”
我说:“对。”
“什么事?”
我问道:“能否向邱老请教,关于解放初期成立总后勤部以及301医院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情况?”
邱会作停下脚步,语气坚定地对我说:“我已明确告知,总后的人员,我一个都不愿见!若要了解情况,我绝无二话,一个字也不会透露!”
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,只需一点火星便能引发爆炸。幸而我已有思想上的准备,内心早已备有几份方案,那就是——沉默。
邱老,我不认识您。我和小朱、小任(邱身边两个人)彼此间都颇为熟悉,我们同属于保卫部一科。在他们的离京之际,是我亲自送他们至山西的高平与河南。
邱会作注视我,坐下沙发。
我继续述说:“那是在1971年5月7日,距离‘9.13’事件恰好过去了三个月有余。在总部的足球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,以纪念1966年毛主席作出的‘5.7指示’。您与您的夫人,还有叶群同志,当时就坐在位于西南角的露天舞台下方的一片草坪上。保卫部的石宝元部长特意安排我站在您的身边,负责您的警卫任务。”

邱会作、吴法宪、叶群、黄永胜、李作鹏。
邱会作的目光紧紧地锁住我。我回忆起当年在“邱叶胡”三位领导身边担任警卫的日子,竟令人惊讶地发现,从头至尾,竟无一位领导同志曾走近他们。
我说:“总后报告是邱老执笔?”
他紧接着回应道:“正是。那篇文章乃我所著,并且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批示。”
我心中涌起一股喜悦,便接着说道:“邱老,关于您及其他三位将领待遇的改善问题,这乃是由吴法宪同志委托我向洪学智首长提出。洪学智首长审阅了我所撰写的关于吴法宪同志的情况报告后,便将其转交给杨尚昆同志。中央对此事已作出决定,并将予以解决。我想邱老对此应该已经有所耳闻。”
邱会作凝神注视着我。沉默。他似乎不愿承认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是洪为他们所策划的。

左一为洪学智
洪与这四位均曾是并肩作战的战友。洪与“黄”先后共同担任过第六纵队的司令一职;在第六纵队期间,洪担任司令,“李”则出任副司令;而在新四军第三师,洪任参谋长,与之搭档的则是“吴”担任的政治部主任。
邱或许也不愿认同那些繁琐的办事流程竟需由小角色来操持。然而,他亦无法对其全盘否定。我坚信,他无法提出任何能够改变他们四人生活境遇的第二个方案。
邱会作陷入了沉默,我也随之微微收敛了情绪。稍作停顿后,我提起另一件往事。“邱老,据我所知,在1970年初,您曾向总理提交过一份报告。”
他缓缓抬起头,目光如炬,直视着我的双眼。我开口道:“请向总理转达我的请求,鉴于总后科技单位众多,恳望能从当前正在部队接受锻炼的大学生中选拔出一批优秀人才,加入我们的行列。”
邱会作直言不讳:“没错,确实如此。那是我亲笔所写。”
我回应道:“总理的批示明确指出,这不仅是对总后勤部的需求,各总部以及各个兵种同样迫切需要。”
邱会作说:“总理这样批示。”
我道:“邱老,近期总后机关迎来了40名新入职的大学生。”
他立即回答:“对呀。”
我回应道:“我正是这40名大学生中的一员。”
邱会作带着惊讶的目光注视着我。这位年轻的小伙子!竟然是我们从沈阳部队精心挑选而来的!
我说:“邱老,这40位学子现已成为机关的军师干部,众人心怀感激,对您和周总理的恩泽铭记在心。”

邱会作与胡敏
邱会作的眼神变得温和,频频点头示意。在四十名大学生中,我独独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。此刻,我感觉他的目光中充满了认可与喜悦。
整个一上午,没有记得那个男服务员给我倒过水。客厅里沉静了一大阵子。邱会作突然发力,激烈地大声问:“你是因回忆录之事而来?”
我点点头。
他猛地起身,语气严厉地说:“提到撰写回忆录,那么我想问,杨立三该置于何地?黄克诚又该如何安置?我们这些人的位置又在哪里?究竟应如何安排?”
我硬是不吭声。
他双手背于身后,脊背挺拔,迈开稳健的步伐匆匆前行。行走间,他语气坚定地述说:“你若询问301医院的创建经过,我便直言,那座医院是我一手筹建的。回想当年,我屡次向周总理请示汇报。”彭德怀归国前,周总理掌管军委。来自协和、湘雅,以及部队野战医院的专业骨干被选调而来。在这些骨干中,主任、副主任以及主治医生主要由这三个渠道选拔产生。骨科的陈景润医生便是从部队调入的。陆为善、何长青等,他们均出自协和医院。
“9.13”事件后,根据叶剑英元帅的批示,总后副部长张汝光(井冈山红军医生)组成工作组进驻301医院,从保卫部把我抽去了,组员还有卫生部和司令部的人员组成(后皆为院校领导)。此后不久,又点名我参加了总后1号首长组织的工作组。

叶剑英
我提交给首长的工作组简报已有所回复,我已仔细查阅。叶帅在原文上细致地划下了每一句的杠线,对于成绩部分,他使用了红铅笔加以标记,而对于不足之处,则用蓝铅笔勾勒。即便是标点符号,也无一例外地被红蓝铅笔勾勒过。这让我前所未有地见识到了首长如此专注地审阅文件的情形。在简报的开头,1号首长留下了“此文写得好”的批示。因此,我对301医院主要医疗骨干的构成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。
邱会作的话语如闸门般敞开,我顿时感到应接不暇。各种信息如同暴风骤雨般“啵啵啵”倾泻而至,其中许多内容并非我撰写回忆录所需。我唯有静心倾听,未敢插言。
他起身送客,重申:“终身不踏总后门!”
我凝视着眼前这位既似曾相识又显得陌生的赫赫人物——前政治局委员、高级将领,心中不禁感到愕然。回想起辽沈战役时期,他曾担任东野8纵的政委;在组建总后勤部时,他又是副政委;后来又升任为副总参谋长,并兼任总后勤部部长。然而,如今他却誓言不再踏入总后勤部的门槛。
我们的首长担任着第六纵队的司令员一职。在平津战役取得胜利之后,首长率领第六纵队六万精兵,于1948年2月16日从香河出发,踏上了南下的征途,目标直指长江北岸的团风。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,首长先是前往南京军事学院深造,随后黄克诚将军被任命为总参谋长,而首长则被委以重任,担任了总后勤部的部长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,首长屡次强调:“此事与庐山无关,林司令亲自下达指令,我岂能不遵从?”
邱会作曾言,他至死都不愿踏入总后的门槛。我心中暗想,自己岂能轻易随口说出豪言壮语:“邱老,不必介怀,请随我回总后吧。我愿亲自宴请您!”面对四目交投的沉默,我们相互敬礼、握手,彼此间流淌着茫然与恍然。最终,我默默转身,离开了他的客厅。
漫步至大雁塔下的招待所,我细细回溯着此次西安之行的点点滴滴,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人类的思想与情感,实则蕴含着共通之处。这股神秘的力量,确确实实存在于世间。尽管情绪可能时而显得截然对立,但只要我们怀着真诚、耐心、善良与善意,总能将其调和,使之融洽无间。次之,今番有幸一睹杜甫心驰神往的皎洁明月,细观他笔下的雄关古道,以及往昔行旅者的足迹之地,唯有与杜老先生未曾谋面而已!然而,杜老先生曾赠我以诗:“闻道长安似弈棋,百年世事不胜悲。”
作者简介
王波,声名显赫的军旅文学创作者,荣获大校军衔,系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,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局的高级秘书。

大的正规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